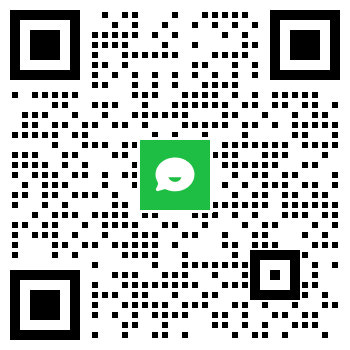河流·田野·工业:珠三角流域艺术驻地漫谈
对谈人 _ 姚明峰 奚雷 彭文彪 一米 易连 谢文蒂 肖剑
珠三角被大大小小的水道切割,密布的河网使得陆地逐渐被侵蚀。从沙田开发到农业生态建设,水陆的交替更迭塑造出城市的历史与记忆,更映射着有关基建、填海等城市议题。河流是庞大而古老的力量,孕育着我们的文明,而洄游则象征着在这里发生的关于生命和文明的独特运动。这种运动依赖于地理环境,更暗含着关于情感、归属、身份、命运、流动与秩序的哲理思考。自2021年起,我们围绕包括中山、佛山在内的珠三角水域的历史与现状展开了田野调查和驻地计划,力图通过走访当地丝厂、甘蔗厂、糖厂、船厂等工业制造地和遗产来理解该地区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以及河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寻访了曾被称为“水上吉卜赛人”的疍家人,感受和想象水陆迥异的生活方式。每一次寻访、行走、对谈与记录,都参与到持续的研究和动态的意义生产中,水自此成为被比拟的介质、与陆地区隔的生活方式、可以被凝固的痕迹以及永不停歇的运动。
驻地创作是一种挑战和协商的过程:“旧”的习惯与“新”的情境、自观的逻辑与他观的联系,既要延续艺术家自己的创作谱系,又要与当地发生真实的关系。在田野调查与艺术表达之间,艺术家们用一种游牧的方式进行探索,再借助自身的生命经验、身体感知和媒介方法,展开关于河流的开放性想象。杉本博司曾用“被曝光的时间”形容他影像中的工业遗产,认为“过度的光线照亮了无知的黑暗”。当我们用新的方法重现那些记忆、技艺、空间时,地方将不再是孤岛,而是沉浸在世界语境中,不断地参与变革、移民、家园等共同议题,最终汇聚成新的联结与想象。本文为“河流计划”在中山格子空间举行的阶段性展览“洄游:从中山到珠三角水域的记忆考古”中的艺术家漫谈系列,艺术家姚明峰、奚雷、彭文彪、一米、易连、谢文蒂和策展人肖剑将从跨媒介视角出发,基于他们在珠三角驻地创作的作品,谈谈艺术驻地、艺术田野中艺术家的角色等话题。单向度地分享作品创作并不是本次漫谈的目标,在驻地中弥漫的情绪或突如其来的想法才是贯穿始终的日常,这些日常点滴汇聚,并由艺术家在每一个节点上再审视、再思考,最终带来全新的创造。
易连,《追光系列之南海丝厂》。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易连:我的这次创作主要聚焦建筑空间和人的记忆的关系。我们走访的这些建筑都依赖于河道的交通运输功能,它们都建在河道边。但具体到每一个建筑,我会针对其目前的空间样貌、曾经的功能和人的关系来进行思考。比如我们走访的中山糖厂、顺德糖厂、南海丝厂等都是早期国营制造业的建筑,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涵盖了人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现在,这些企业要么转制了,要么变成了空壳,仅仅留下了建筑本身,或者说这些建筑成了另一个载体,唯一还保留了以前生产方式的就是南海丝厂。
像《追光》这个系列,当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观察这个建筑的时候,会获得很不一样的视角和感受,因为我们不是其中的一分子,从俯瞰的角度观看,我们跟它有一种对抗性,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只能通过一些非常简单或概括性的方式去接近。我们跟这些建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在晚上用一束像舞台的追光灯一样的强光,从一个非常远、非常高的角度把建筑里面的每一个角落照一遍,像一种审视,或者说窥探、关怀;另一方面,又像是主动操纵一种东西进入它。当用光去打量这些建筑的角落时,它们像是人造的灯塔。比如说为了在舞台上呈现一个建筑,一般会用纸板做一个剪影,勾画它的轮廓,把它立在舞台上,告诉观众那里有一栋建筑。虽然我们知道舞台布景是假的,但它让你以为它是真的。我设想去用某种我们熟悉的方式去靠近这样一个东西,建筑也好,留给我们的建筑图像也罢,虽然它在发挥着某种功能性,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已经不是功能性的了。比如,原本糖厂所在的建筑已经不是糖厂了,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的图像,这个图像是扁平的,正如你晚上在屋顶上看到的厂房的轮廓一样,它只是一种扁平化的东西。
易连,《剥落合成》。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肖剑:易连刚提到艺术是一种图像化的视觉方式,也提到了关于遗产、建筑的一些感受,你觉得呢?
谢文蒂:我跟易连的切入点很不一样,他关注空间建筑的外部、内部关系,还有人和建筑的联系,其实都是以一种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我的切入点可能会更微观。我对丝厂最有印象,因为相比糖厂、船厂,丝厂是一个还在生产的地方。我想做的创作是从丝厂女工的手切入,我注意到她们在庞大的车床前上下翻飞的手势。当发现丝厂里基本是女工在操作台上工作时,我就觉得这和我用的玻璃材料是一种巧合——玻璃也挺像女性,这种材料非常敏感,用它去做关于丝厂的作品还挺合适的。但我并非要去强调一个女性视角,或者说女性的状态。我给她们劳作的手翻模后,可能已经看不太出来是女性的手了,而是一双劳作的手,它的指关节也许很大,非常直观,然后我把这个手模放在玻璃里——我一直坚持要用透明玻璃的负形去表现,而不是做一个实体的手,里面是空的,同时形态又清晰可辨。因为在女工工作的过程中,最吸引我的是她们长年累月在做的几种手势,看上去似在翻飞舞动,很轻柔,又非常有力量。从某种程度来说,既虚空又实在。
我觉得这些都很有力量,但又是一种特别温和的力量,就像河流之于人类。一直以来,我觉得河流在人类文明里扮演的更倾向于一个女性角色,它默默孕育、滋养、洗礼着人类社会。我想做的另外一组作品是关于痕迹的,其实也与记忆和劳作很有关系,因为劳作会留下很多印记,比如说给女工的手留下的印记。我们看到的建筑里的所有痕迹都是这几十年来人们在此生产劳作所留下来的,不管是机械设备,还是人的活动、水蒸气等留下的痕迹。这些我们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痕迹形成了一个建筑空间特有的肌理,成了它和其他建筑物区别开来的模样,这个是很有趣的。
谢文蒂,《游丝》(2022)。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易连:从谢文蒂开始有这个想法到她最后做出作品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私下里也讨论了很多。她首先关注跟人发生最直接关系的物件,其次是手和劳动的关系。我觉得她抓住蚕丝和手这个点特别对,因为它们都是非常敏感细微的东西。之后,她也有一些其他创作想法,和茧、玻璃球也有些关系,但我觉得手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从手的姿势到手指或手跟茧的关系,比如蚕丝会把手割破,它们之间有一种柔软又锋利的关系。
谢文蒂:我听女工说,别看丝轻柔,实际上经常会把手指割出口子。
易连:手、蚕丝和玻璃的关系里能发展出抽象化的表达,因为玻璃本身有一种特权,即用别的材料可能没办法这样去表达,比如说用玻璃表达空,谢文蒂的说法是“给空气描边”。
肖剑:当易连在拍影像时,谢文蒂跟我讨论了一下,说觉得这种拍摄方式比较有意思。你说影像艺术家时,是把它放在某种定义之下吗?
谢文蒂:没有,我当时想说的是用田野调查这种工作方式来生成作品,影像艺术天然地适合,它适合用来记录一个大的环境。
肖剑:但易连不太喜欢“田调”这个词。
易连:要这么说的话,研究型的艺术家更适合做田调。不是说不喜欢,只是我会把田调当成一种材料去处理,而不是当成作品本身。有的艺术家田调完就直接把文献展示出来,像档案馆一样。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就像 《脱口秀大会》里的选手直接用谐音梗一样,也不能说没有动脑,就是来得太简单了。一些研究型艺术家肯定会说,你以为做纯艺术简单,这就是艺术?当然,关于什么是艺术肯定是有争论和讨论的,这本来就是艺术的样子,就看你想秉持怎样的态度,要坚持怎样的工作方式。
谢文蒂:但其实我是喜欢易连的这种方式的,不是说研究型的不好,但我会觉得它们非常“实”,没有什么弦外之音,没有太多想象空间。我比较喜欢不那么定性、比较模糊、似是而非的东西。
谢文蒂,《游丝》(2022)。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肖剑:怎么会想到创作《水上怪谈》?在这个作品里,你们把大家带到疍民在岸上歇脚的角落,听在一个疍民身上发生的寓言故事。是否觉得对于在陆地上生活的大多数的人来说,疍家人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存在?
一米:是的,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水上神话民间传说大都来自陆上人的想象。而一个常年和江河打交道的水上人对水并没有那么多猜疑,一是因为他们本身对水已经很了解了,在他们看来,传说中的水怪很多时候只是大鱼或其他海洋生物;另外,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习惯与水中的未知共存。这让我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始于陆上的有关“毛人水怪”的传说(后来成为影响力很大的一个谣言),正是某种“不可捉摸”。
肖剑:请分享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疍家人的故事。
一米: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平凡的故事,只是相对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比较不一样而已。在这种周期不长的走访过程中,我只能从一些个体自述的经历中看到这个群落特有的生活经验和遭遇,他们的口述会加深我对在文献中阅读到的某些信息的认识。印象比较深刻的个体应该是我在东莞虎门太平遇到的一个大叔。他说以前一些陆上人因为太穷,养不起小孩,水上人就会收过来当自己的孩子养大,毕竟在水上吃饱也不是难事,这个大叔就是这么过来的。他6岁开始上船跟着养父母生活,大半辈子到处打鱼,如果不是遇到台风,他们可以几个星期都在海上漂着,哪里鱼多,船就开去哪里。他感慨着时代的变化,感慨现在反而不比以往那样来去自由,“怀念旧时两个证件走天下的日子”。
彭文彪、一米,《水上怪谈》,影像截图。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彭文彪:我们喜欢收集很多相关的素材,然后去重构某种东西,但这种重构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不是说要像田野那样去复原,这个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肖剑:有时我们谈怎样进行艺术乡建,就是要重新复苏某种仪式或者某种东西,好像可以借此重新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但我觉得艺术好像并不需要这种功能。这让我想起一位学者讨论过的有关艺术自律和他律的问题,说其实很多时候艺术家并不会去考虑艺术和社会有没有产生关系这个问题,他并不是通过外界的规则去限制或促使自己去做作品的,而是通过自律的方式去构成自己的艺术作品的脉络,这就是艺术的自律问题。他律则是指社会环境以及艺术家跟市场的关系,比如商品化的大趋势。
彭文彪:当然,艺术家做艺术的时候肯定想要被认可,但这只是一种浅层的意义,我觉得做艺术最深层的意义是要对得起自己,要问:我要做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在哪?好的艺术作品不一定会在当下跟社会有一种对接或连接,但等几十年后回头看,会发现里面有一种先验性,比如白南准(Nam June Paik)的作品。有一年,我在深圳看到白南准的录像,我很惊讶,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组装的机器人可以在大街上行走,虽然机器人做得很粗糙。再来对比今天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的机器人,你就会感觉未来可能真的是这样子的。但白南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这么想了并且实践了,是以艺术的方式在“实践”。
肖剑: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比较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在某一时刻能够和观者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不是一种被安排好的情绪,而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情绪。
彭文彪:有时我们走在大街上或坐公交时会想到一个方案,有时很想把看到的某一瞬间做成一个作品,我觉得这种研究是一种思维惯性。
彭文彪、一米,《水上怪谈》,影像截图。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一米:惯性使我们更了解某个媒介,去开启这个媒介更多的可能性。我不会刻意去选择或不选择一种新的媒介,在做某个项目或作品时最终选择什么媒介,很多时候还是取决于作品本身要表达的内容的质感。此外,媒介的选择和组合还会受我和搭档在特定作品框架下不同表达的搭配有关,会比个人创作多一层考虑。
肖剑:在接触一种新的媒介时,会不会有异样感?
彭文彪:这当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思考:一个成熟的想法肯定要附带一种成熟的展现方式。
一米:会的。我本来是学油画的,影像这种媒介曾经让我有过异样感,但如果把某些表达硬塞进画布,异样感反而可能会在画布上出现。
姚明峰:我之前的部分作品是有关数字图像的,思考如何在当代解读数字图像。我们现在用手机拍摄图像太便捷了,图像总能传递出一种非真实的景观。我想通过技术手段将数字图像里的“数字”剔除,所以在作品中呈现的是黑白图像与被分离的颜色的一种并置。
肖剑:你怎么理解数字图像和驻留的关系?
姚明峰:我觉得驻留期间的作品,以及在当地所拍摄的图像、所观察的事物,和当地语境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在工作室则一般不会受到当地一些文化符号的直接影响。
肖剑:你认为这次作品中的哪些元素体现了这种驻留感?
姚明峰:我在拍摄时刻意强调画面的构成——这是我在现场的一种感受,以及沿河收集渔民生活痕迹的材料、录制现场的声音等。
姚明峰,《测试》系列作品之深圳填海区域(2021)。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肖剑:你的创作方向是对数字图像的批判或质疑,那么你之前对诸如深圳填海的关注是否也在这个框架里?
姚明峰:对,填海是我作品的主题之一,其中一些元素也和图像有关,对数字图像的质疑是在做有关填海的作品时引申出来的。在查阅有关深圳填海的历史图像时,我发现其与当下图像的关系不仅仅是围填前后的物理变化,更是一种化学变化。
肖剑:也就是说,这种变化是可能存在的,不可模糊的。
姚明峰:对,在收集素材时,因为有一些精确的数据在档案中查询不到,我就以另一种方式去收集。例如,利用地图的卫星图像、现有的地理坐标以及去现场收集材料等。我觉得“写生”这个词更适合用来描述我的创作,因为它意向的东西会多一点。这和田野调查不同。我觉得田野更严谨理性,偏向于研究型的创作者。但在西方,对于艺术家田野也有不同的理解,一些美国艺术家会采用更偏人类学、社会学的工作方式,但最后呈现的方式以视觉为主,不会让观众误以为进入了一个研究所的方案厅,他们所做的研究只是作为一种创作素材及生成作品的过程。田野的形式也取决于艺术家对其自身创作方法的定义,就像艺术家定义其作品的属性一样。
奚雷:我觉得很多艺术家用的方法还挺艺术的,和民族志的调查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他们有时会更重视一种情感和感官上的相遇。
姚明峰:对,创作方法和形式还是要取决于艺术家自身,创作始终要回归视觉和感官,而这种感官是宽泛的,无论是以文本还是别的形式呈现。
奚雷:我觉得分析理论依然很有帮助,只是怎样让理论在创造里起到激发而非限制创造性的作用,这更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本质性矛盾的问题。
姚明峰:有时理论本身就是框架和边界,我觉得创造性就是需要去打破框架和边界。
姚明峰,《测试》系列作品之深圳填海区域(2021)。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版权声明:本文由东莞厂房网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部份内容收集于网络,如有不妥之处请联系我们删除 400-0123-021 或 13391219793